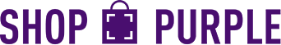1998年5月,儿子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,我们正准备参加他的毕业典礼,这本该是我们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。然而,我父亲很快就会死于胰腺癌,这让我的喜悦蒙上了阴影。
和许多人一样,在迈克尔·兰登(Michael Landon)公布他的诊断之前,我从未听说过胰腺癌。从小看《Bonanza》长大的我对“小乔”非常喜欢,听到他生病的消息时,我感到非常难过。然而,直到我父亲的诊断,我才明白它的全部影响。我仍然记得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永远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消息时说的话。他不敢正视我们的目光,叫我们回家去,把父亲的事情安排好。
我们难以置信地问了几个典型的问题:“化疗、放疗或者更多的手术怎么样?”我们还能为父亲做点什么吗?”虽然医生说他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生命,但这个可爱的人连一个月都没活下来。叔叔去世后,他提到我的祖母也死于胰腺癌。
2002年,当我们还在从失去父亲的打击中恢复时,我们的家庭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毁灭性的打击——我叔叔的去世。他几乎是我父亲的翻版。像我父亲一样,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不舒服,也从来没有翘过一天班。然而,他又一次让我们回家,把他的房子收拾好。在他被确诊几天后,我的叔叔死于同样的疾病,就像他的母亲和他的哥哥一样。
我的三个家庭成员都死于胰腺癌,这令人震惊。这怎么可能呢?我的儿子们怎么办?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?我不知道答案;只有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当我出现一些模糊的症状时,我问医生这是否可能是癌症。“别担心,可能只是溃疡,”他说。结果出来的时候,他还没说话我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我认出了父亲的医生对眼神交流的回避。他告诉我,我很幸运:肿瘤很小,而且发现得早。如果我立即开始治疗,我会比大多数人有更好的机会。
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两个词:“胰腺癌”和“不可手术”。我立即开始化疗,并接受了短时间的放射治疗。因为我的早期诊断,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人的支持,以及上帝的恩典,我今天仍然在这里讲述我的故事。但这种疾病仍然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:我母亲在2005年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。我们一起继续战斗。
当我父亲最初被诊断出这种疾病时,我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。不幸的是,当时没有胰腺癌行动网络可以求助。我在网上搜索,发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在线讨论小组。在那里,我遇到了一些和我一样对缺乏信息感到困惑和沮丧的人。
通过这个组织,我认识了(胰腺癌行动网络的创始人)帕姆·阿科斯塔·马夸特,她的母亲死于胰腺癌。她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,也很支持我。在这段时间里,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安慰,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善良。由于最初的接触,我发现自己在每次诊断后都求助于胰腺癌行动网络。
2008年3月,我参加了该组织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二届年度倡导日。在那里,我遇到了两位最好的朋友死于胰腺癌的年轻女性。我对他们的奉献和承诺感到敬畏。和我一样,他们也来自加州奥兰治县,邀请我参加一个会员会议。听到他们激动人心的故事,我意识到我必须做点什么,所以我加入了奥兰治县联盟,担任他们的媒体/公共关系代表。我还通过支持PanCAN患者服务网络与他人分享我的经验。
我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——我既是一个看护者,也是一个幸存者,我两面都经历过。通过我的经历,我现在给那些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的人、幸存者以及宝贵的照顾者带来了希望。我想有所作为,以便有一天,没有人再听到“回家,把你的房子整理好”这句话。
罗伯塔露娜
奥兰治县,加州

 877-272-6226
877-272-6226